本书收录了思想家柄谷行人自20世纪末以来的一系列讲座文稿。作为当代东亚少数具有广泛国际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之一,柄谷行人的著作在中文世界里已经获得了为数可观的介绍、翻译和研究;这一时期的时代脉络,以及作者身处其中的思想历程,也已在书中最后一篇演讲稿《移动与批评——跨越性批判》以及《关于思想地震》里有了详细的自述。综上种种看来,或许译后记实属蛇足,但为了在书末获取一小块可用于致谢的位置,译者不得不设法作出一篇有其存在价值的文字来。
正如《关于思想地震》一文所述,本书收录的这些演讲稿内容大多是对作者自己理论著作的解说,而较少有另起炉灶的新主题,或是临场阐发的新思想。因此,如果读者对柄谷行人晚近的思想已经很熟悉了,那么本书或许会显得颇为浅显;然而换个角度来看,对于那些希望入门柄谷思想ABC,却苦于没有时间精力阅读那一排大部头的读者而言,这本演讲集则能够成为非常合适的导论。相对于维持了必要之艰涩的那些理论作品而言,这些晓畅通达的讲稿排除知识储备上的障碍,能帮助我们更顺利地进入柄谷的思考语境。而如果读者希望深入了解柄谷在某问题上的论述,则可在掩卷后进一步阅读该部分对应的相关著作。译者希望为此提供一些便利。因此,我将在下文逐一列举本书收录的各篇演讲稿与柄谷主要著作之间的对应关系,并概述其主旨和当前意义。此处所列作品以已有(简体或繁体)中文翻译的著作为主。
《地震与康德》《作为他者的物》——《跨越性批判》《伦理21》
起首两篇讲座的核心内容,无疑可以视为《跨越性批判》一书的主旨提要。作为公认的新世纪以来柄谷思想的定调著作,该书的出版标志着柄谷正式走出后现代主义窠臼,开始了一种朝向未来的哲学、社会和历史理论的建设性思考。在1989年出版的《探究II》中,柄谷还在践行一种解构性批判,他当时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或许最好地体现在他反复引用的这一段话中:“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换句话说,当时的柄谷不追求确立某种具有潜在可能性的未来目标,而是尝试根据当下社会实践的实际需要而灵机应变地重构文本,以此展开对现状的批判。而在1995年的《地震与康德》中,柄谷已然开始了批判性的重建,并把其探索对象的马克思和康德确立为进行“发现和缝补裂痕的决死尝试”的现代思想家。这一探索的成果凝结为《跨越性批判》。在该书中,柄谷不但聚焦于康德和马克思思想中的“移动”(基于空间、视角转变而产生的视差式的批判),还反复在康德(伦理)与马克思(经济)之间来回移动,展开一种综合了先验论(transcendental)和横跨各领域(transversal)的理论批判。另外,关于本演讲中涉及的伦理学问题,可以参考《伦理21》中的论述。
如果《地震与康德》可称为“建设宣言”,那么《作为他者的物》则是“反抗宣言”,也是“日本后现代之左转向”中的一个关键文本。此文明确地申明了《跨越性批判》等理论著作的实践方面,在于站在后冷战时代的现状中,寻求替代现存资本-民族-国家体系的可能性。[1]
不过这里需要立即澄清的是,柄谷并非在试图重新确立一种支配性理念。作为日本新左翼传统的一员,批判那种将主义之实现视为历史必然的、目的论式的理念,毋宁说是柄谷的理论及实践活动的出发点。然而在苏联解体后,在日本不但那种自上而下的变革理念土崩瓦解,人们甚至开始对任何值得追求的理念怀抱反讽的态度。右翼和左翼在这一点上桴鼓相应,展开了名为“历史终结”或者“宏大叙事之终焉”的齐声合唱。[2]面对这一情况,柄谷强调了康德哲学中“建构性理念”和“整合性理念”的区别,指出不同于把理性用于未来目标建构的前者,后者仅仅作为可能性而存在,因而不过是一种“假象”;然而如果没有这种假象,我们便无法前行。整合性理念因而并非作为压迫观念存在,而是在展开对抗现存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运动时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一种可能性的契机。而对这一理念的考察,便导向了《跨越性批判》最初提及,并在后来的各著作中逐渐获得深入讨论的核心概念“交换样式D”。
《现代文学的终结》——《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历史与反复》
这是本书中篇幅最长,或许也是最具分量的篇目之一。在发表之初,柄谷对现代文学开具的这份“死亡报告”曾经一石激起千层浪,在日本乃至韩国的文艺评论界均造成巨大反响,并引发了有关文学之去留存亡的广泛讨论。在中文世界,柄谷往往是以文学评论家的身份为人们所知的;然而这一关于“文学之死”的著名论题却鲜少有人提及。在其发表近二十年后,这篇讲稿终于被译为中文。
本讲稿内容并非对此前著作的解说,而是在讲座过后,连同围绕该主题的座谈会文稿被整理成书(『近代文学の終わり——柄谷行人の現在』,INSCRIPT,2005年)。不过,为了深入理解柄谷在本文中对“现代”“文学”及其“终结”的定位,我们可以回顾他在《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中的讨论。另外,本文中围绕现代文学确立过程的历史性、结构性考察,有不少沿袭了《历史与反复》一书中的分析。
时至今日,柄谷所指出的诸多情况确乎已成为我们司空见惯的景象。随着符号生产体系日益商品化、细分化,那种肩负社会整体的道德责任,能够成为“处于不断革命中的社会的主体性(主观性)”(萨特)的“现代文学”,在今日已难寻踪迹。说白了,那样的现代文学早已为民族国家和消费市场所抛弃。而柄谷在现代文学(小说)的终点上回首其确立过程,是为了指出文学已经完成它被赋予的历史使命,因而即便寿终正寝了,也不值得哀叹什么。因为“终结”的是承载一切、推动变革的文学,而并非变革志向本身。相反,变革的希望正蕴藏于点滴的生活实践之中,这也正是柄谷离开文学,走向社会实践领域的原因。
《日本精神分析再思考》——《民族与美学》、《日本精神分析》(尚无中译)
这篇演讲的主要内容脱胎于1992年的连载评论《日本精神分析》,分五期发表在思想刊物《批评空间》上。正如本文中作者的自述,这一项考察的目的,是延续丸山真男、竹内好等战后思想家所进行的对日本文化结构的批判性考察。但是这些连载评论并未集结成著作出版。到1997年,柄谷在《再论日本精神分析》一文中回顾了这项研究,此文经过改写收录进《民族与美学》一书。
《日本精神分析再思考》便是作者对上述这些1990年代初期工作的回顾,因此,它也成为新世纪以来柄谷为数不多的有关日本社会、文化的发言。通过将世界体系论式的“中心-周边”视角纳入对文化现象的思考之中,柄谷尝试从日语的比较地缘政治学特征入手,对被称作“日本式的东西”展开批判性的再探讨,而又不至于陷入“日本人论”那样的本质主义。
在此前的2002年,柄谷还出版了一本名字相仿但内容不尽相同的演讲集《日本精神分析》。该书内容虽说也与本讲座的问题不无关系,却是出于很不同的考察宗旨。《日本精神分析》一书中收录的各篇讲座均发表于《跨越性批判》出版之后。此时,柄谷已经确立了基于交换样式论的分析构架,并着手展开对“民族”与“国家”之成立基础的深入的考察。与之前阶段对日本文化结构特点的考察不同,此时的柄谷更加关注的是如何超越思维中的本民族中心主义,基于日本的特殊经验来思考普遍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建构问题。换句话说,《日本精神分析》中虽然讨论的大都是明治日本的情况,其目的却是旨在从该事例中探索“资本-民族-国家”三位一体结构的普遍确立过程,并探索别样可能性的契机所在。
《重新思考城市规划和乌托邦主义》——《作为隐喻的建筑》
如果阅读中译版《作为隐喻的建筑》便会发现,柄谷为其写作的序言,内容相当于本篇演讲稿的一个底本。然而,《作为隐喻的建筑》一书的接受史可谓一波三折。该书单行本发行于1983年,收录了1980年代初期以来,作者身处日本后现代主义思潮的风口浪尖,围绕形式主义及其悖论的问题所展开的理论思考。然而这么一本哲学和知识批评著作,却旋即被纳入建筑设计领域而得到阅读,给相关从业人员造成了很大困扰。
值得注意的是这本著作在柄谷个人思想史中的定位问题。翻开1983年出版的单行本,会明显感受到那个时代不受体系观念束缚,强调即时性、“施行性”的批判风格,纳入的文章随意奔放、不拘一格;1989年的文库版中,虽然已删掉了六篇私人随笔性质的短文,却依然保留了后现代主义时期柄谷的思想和文体。然而2004年岩波书店所出版的《定本 柄谷行人集(2)作为隐喻的建筑》一书,却是与1980年代的同名著作大相径庭的作品。定本版在内容上可说是对1983年《作为隐喻的建筑》与1985年《内省与溯行》两书的集成。然而经过作者的重新编排以及逐字逐句的改写,定本版内容正如同其腰封文字,是“此前未有,从今往后才开始存在于世的一部作品”。也就是说,改写过后的岩波定本版《作为隐喻的建筑》已然站到了《跨越性批判》同样的思想立场上,甚至在很多地方超越了后者而有了全新的展开。
从《重新思考城市规划和乌托邦主义》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此时柄谷的思考早已超越了后现代主义的射程,而开始揭示一种取代自上而下式规划主义的、别样的乌托邦主义的可能性。因此译者想要在此提醒,基于岩波定本版翻译的中文版《作为隐喻的建筑》,绝不能作为反映1980年代柄谷思想的作品来阅读。那是已然从那个位置经历多次“移动”之后的结果。而将《思想地震》中收录的这篇晚近讲座内容视为该书导言,或许正是恰如其分的。
《日本人为何不游行》——《柄谷行人谈政治》
发表于2008年的本篇演讲,是《日本精神分析再思考》之外另一篇主要针对日本社会和政治结构的考察。在讨论日本为何缺乏公共参与的问题时,柄谷参考了丸山真男、久野收等人的主张,从历史性、结构性因素出发探究其原因。从本篇中可以发现,在脱离后现代主义之后,柄谷的政治立场上开始向力求在日本确立市民公共参与的战后知识人的观点靠拢。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柄谷在引用丸山,重申战后思想之意义时,并非旨在确立一种基于原子化、均质化个体的国民共同体。曾有研究指出,以《个体析出过程的种种模式》一文为标志,丸山真男关于近代的理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不同于前期那种雅各宾主义式的近代国家观,丸山在此后更多地开始重视教会、行会等中间团体在形塑近代主体过程中的积极作用。[3]而柄谷在这篇演讲稿中所重新发现的,正是这一后期丸山所具有的当下意义。包括新联合主义运动(NAM)在内,从柄谷自身的政治实践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对串联个体来形成对抗性力量的中间团体的重视。我们可以在这里发现一条日本战后思想传承的隐秘线索。
在本讲座发表一年后,柄谷曾在一次长篇采访中,畅谈自身从安保运动的学生活动家出发直至今日的整个思想-实践历程,并基于这样的经验阐明自身对当前左翼实践的主张。柄谷认为,在对抗新自由主义的左翼实践中,有必要形成一系列的小规模联合体,并寻求形成相互之间的合作网络(联合之联合)。该访谈既是对本篇讲座中所述思考的扩展,也能帮助我们联系柄谷的人生经历来对其加以理解。这篇访谈后来收录在《柄谷行人 政治を語る》和《政治と思想 1960—2011》两本书中,中译则有《柄谷行人谈政治》可供参考。
《秋幸或幸德秋水》——《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
在本篇讲稿中,柄谷从中上健次笔下的小说主人公秋幸与幸德秋水之间的渊源说起,提示了日本近现代文学与社会运动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从而在作者的成名作《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之外提示了一条文学史的新线索。当下看来愈发明显的是,《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一书分明是一个批判后现代主义的先驱性文本。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书中指认“日本现代文学”之“主流”,也即从坪内逍遥、国木田独步直到村上春树的谱系,事实上是一个将视角不断聚焦到无关紧要的“风景”之上的消极避世者的传统。他们虽然并未支持强权,并试图消解那种宏大叙事,然而到头来却只是瓦解了抵抗的能量,并从旁支持了强权的延续。如果这种“日本现代文学”是作者反讽性地提示的反题,那么本篇讲稿则铺展开了其正题,也即从明治二〇年代(19世纪末)帝国主义时期开始的近现代历史中,文学家与行动者们交错联结、难分彼此,不断向现实中的不公奋起抵抗的线索。
有必要补充的是,如果基于柄谷关于资本主义历史的一百二十年周期说来思考,下一个与明治二〇年代对应的时期,正是我们身处的当前时代。的确,小到旧区改造和生活世界的商品化,大到福利制度的退潮、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兴起,乃至国际关系从合作转向敌对、国家间的集团化与相互角力……文中所描述的那个年代的种种情状,在改头换面之后正一一再度粉墨登场。另一方面,在当下左翼的思想和实践中,无政府主义也正在经历着一轮引人瞩目的全球复兴。柄谷对这一历史的回顾,自然不仅仅是在翻陈年旧账,而是对当下所有思考着的行动者们构成了警示。警示的内容或许便是那句耳熟能详的话:那些无法从历史中吸取教训的人们注定要重蹈覆辙。
《帝国的边缘与亚边缘》——《帝国的结构》
这篇演讲可视为对《帝国的结构》一书的入门级解说。在考察韩国、日本等东亚社会前现代历史发展进程时,柄谷尝试纳入“世界—帝国”这个长时段史/世界体系论视角,以同“中心”的中华帝国之远近关系为着眼点,来思考决定不同社会的历史走向以及文化脉络的结构性因素。然而或许是受限于演讲主题,本篇演讲未能涉及该著作的核心问题关切。事实上,《帝国的结构》仍旧延续了从《跨越性批判》《世界史的构造》以来的实践志向。柄谷之所以将目光转向“帝国”,是为了从诞生于其中的普世宗教那里,发现能够扬弃当前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突破口(即超越资本—民族—国家连环的交换样式D),并借此重新想象可能的世界图景。因此如果希望充分把握这一意图,可以进一步阅读《帝国的结构》中的论述。
《哲学的起源》的相关演讲——《哲学的起源》
本篇演讲要言不烦地概括了《哲学的起源》一书的主要内容。在该书中,作者通过对前苏格拉底哲学之伦理层面的探索,揭示了伊奥尼亚社会中“无统治”(isonomia)理念的存在。在柄谷看来,与雅典城邦中那种压制自由的“民主主义”不同,在“无统治”状态下,正是(移动的)自由保障了平等(民主)的实现。从苏格拉底拒绝参加公民大会,而是在广场(agora)上参与公共讨论这一事例,作者引申出了有关哲学起源考察的当下意义,也即认为代议民主制必然需要议会之外的assembly作为其必要的补充,否则便只会沦为贵族统治的工具。然而关于“无统治”的历史成立,以及它如何是基于一种自由人之联合(交换样式D)而成立的政治-伦理体系,就有必要参考《哲学的起源》一书中的详细论述了。
《山人与山姥》——《游动论》(尚无中译)
从2014年出版的《游动论》中,可以看出柄谷晚近思考的方向性。这部作品聚焦于柳田国男笔下的山人(游动的狩猎采集者),指出山人与从平原移居而来的山地民之间的区别,以探求当下社会变革的主体可能性。不同于高度契合跨国资本运作模式的山地民,山人之中包含着超越现存资本与国家体制的契机。这是因为山人包含了“原游动性”原理,也即对恢复到自由和平等状态的强制——在定居革命之后,这是通过基于互酬原则的礼物交换而实现的。
然而事实上,自柳田写作《远野物语》的时代起,他笔下那些“山人”的真实性便一直饱受质疑。日本学界普遍认为“山人”从未真实存在过,而仅仅是柳田在东北地区民间故事基础上的想象。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原游动性仅仅是一场幻梦,变革主体本就是不可能的?
其实在柄谷那里,“山人”是否真正存在根本无关紧要。重要之处在于,围绕“山人”的传说和讨论,其本身是某种无意识驱力的浮现。也就是说,柳田所执着的并非山人的存在,而正是原游动性本身,且这或许并非柳田本人的主观意愿,他不由自主地便这么写了。柄谷借用后期弗洛伊德的说法,将那称为是原游动性作为“被压抑物的回归”。虽然无法在当前社会体系中找到自身位置,“原游动性”却会如同强迫症般执拗地经由无意识作用而浮现。正是在这里,柄谷发现了迈向变革的必然契机。从这个意义上说,《游动论》虽带有“变革主体论”的外观,却又构成这类讨论的反类型,因为它瓦解了对变革主体(工人、学生、知识分子、“诸众”……)的单纯指认,而将其归结于全体社会成员都可能具有的潜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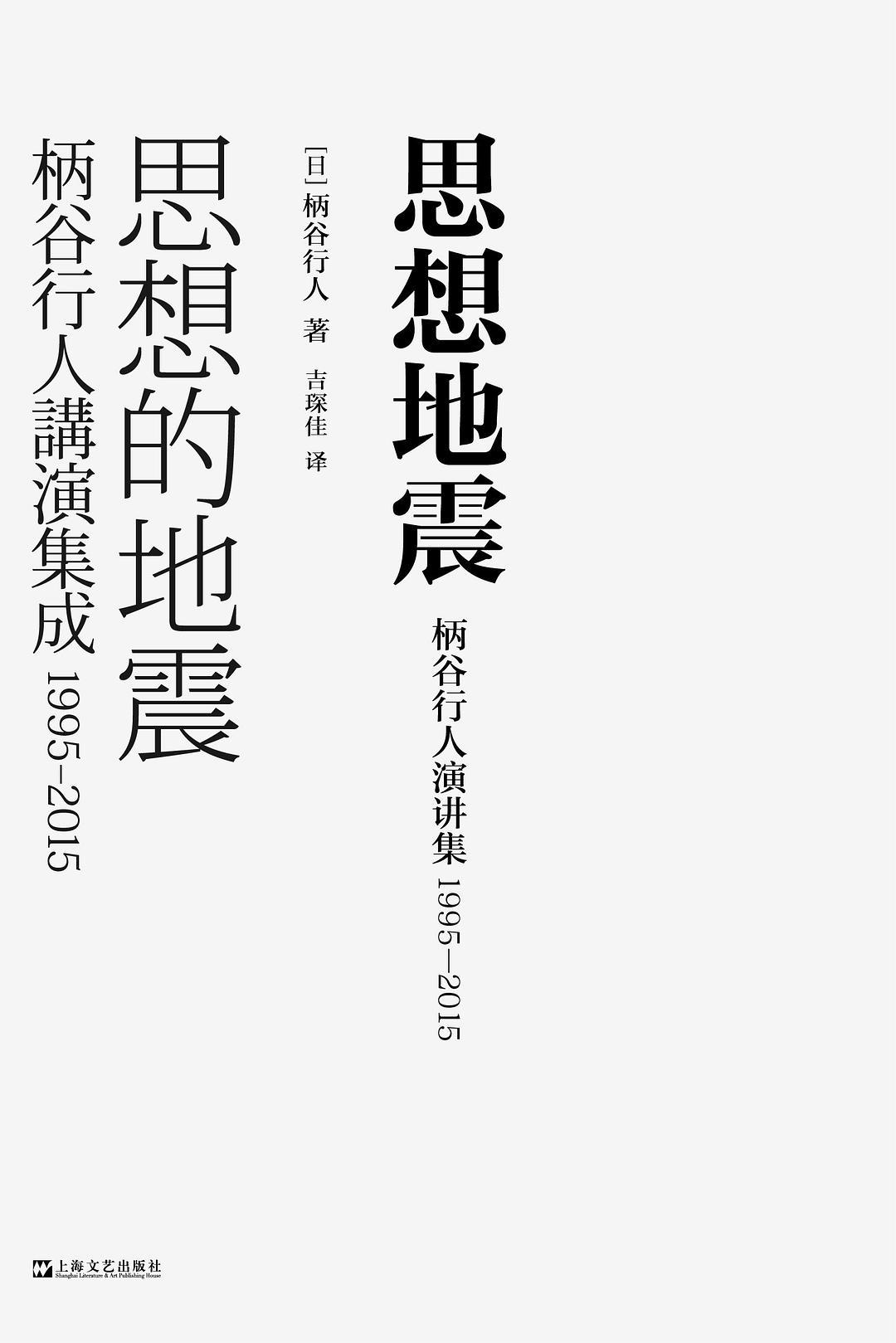
除了这些个别篇目与著作间的对应关系之外,这里的讲座都或多或少触及《世界史的构造》一书的内容。该书以最具体系性的方式,展现了本演讲集所涉时期柄谷思想的基本框架。因而为理解这一时期的柄谷思想,该书在重要程度上或许超过了上述所有著作。
以上便是译者基于自身理解,对各篇演讲稿的内容提要及相关文本介绍。这当然不是解读这些作品及其关系的唯一方式。译者只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梳理工作,为读者进一步阅读和理解柄谷思想提供一些帮助。
最后,感谢上海文艺出版社的肖海鸥老师、《上海书评》执行主编郑诗亮老师,是他们的热诚和周到才使得本书的出版成为可能。我也想感谢以下各位在百忙之中抽空审阅译稿的师友(排名不分先后):黄诗琦、陈诗雨、言语、占黑、路平。柄谷堪称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此处讲座的主题也不一而足,涵盖了文史哲、社科乃至城市规划等领域,令译者的知识储备时常捉襟见肘,幸好还有这些朋友们提供的专业建议。此外若非他们的指点,一向粗枝大叶的译者也将无法发现草稿中的种种疏漏。
上海的定海桥互助社在去年经历拆迁搬到了线上;而在东京高圆寺,素人之乱的大笨蛋宿泊所也因新冠疫情而暂停了营业。然而与表面上的低潮相反,一张“自由人之联合”的网络业已在各地铺展开来。如果没有这些现实中存在着的替代性实践,译者对包括柄谷在内的社会理论的关注和探索也将会是无源之水。而反过来,这样的参与、思考,或许也正塑造了现在的这个我自己。借用本书中提示的丸山的框架来说,只有当身处这些自由而又团结着的人们之中时,我们才得以既不屈从集体权威(民主化),又不自闭于私人的小世界(私人化),更不至于成为随波逐流的盲众(原子化),而得以实现真正的“自立”。借此向各位长久以来给予我无数触动和启迪的大笨蛋们表达谢意,谢谢你们的存在。
吉琛佳
2022年元月1日于京都一乘寺
注释:
[1] 对于这一思想转变的过程,柄谷曾在许多地方提及。如可参见2018 年的讲座《资本之“力”与跨越资本之“力”》(黄边站HBSTATION 公众号,2019 年10 月24 日、26 日)。
[2] 关于这一时代背景较为详细的介绍,也可参考《911 思想考古丨柄谷行人:这并非预言》一文的译者导读(《澎湃新闻·思想市场》2021 年9 月16 日)。
[3] 参见三宅芳夫『ファシズムと冷戦のはざまで:戦後思想の胎動と形成 1930-1960』。
(本文为《思想地震》译后记,澎湃新闻经出版社授权刊发)









 蜀ICP备2022028980号-1
蜀ICP备2022028980号-1